电话:020-66888888
人文主义者伯纳德·威廉姆斯:乐观但不幼稚,悲
作者:bet356在线官方网站 发布时间:2025-11-10 0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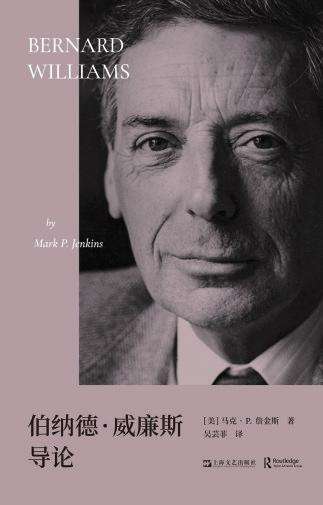 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科林·麦金称伯纳德·威廉姆斯为“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灵魂的分析哲学家”。尽管对于什么是人文主义者众说纷纭,但对威廉姆斯来说,一个称职的人文主义者必须深刻理解思想所处的历史情境,理解不同价值主张的重叠和冲突,看到人性的复杂性和正义的限度,接受和包容理论中不断溢出的异质成分。在“理论”基础上相互竞争的哲学家们认为,异质性因素是哲学必须克服的障碍。在威廉斯看来,哲学的“智慧”恰恰在于发现和尊重那些超越理论界限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丰富维度——比如忠诚、爱、遗憾、独特的个体叙事、无与伦比的失落、无与伦比的感受。的生活。在《伯纳德·威廉姆斯导论》(以下简称《导论》)这本对伯纳德·威廉姆斯思想的精彩介绍中,作者詹金斯不仅能耐心地研究剥茧的过程,还能将细节仔细地编织成一幅总体的思想图景。他不仅忠实地呈现了威廉斯思想的原貌,而且从高处做出了公正的定位,表明他既能看到树木,又能看到森林的理论实践。更重要的是,詹金斯的叙述充满温暖。在保留这本书的同时,我们不仅了解了威廉姆斯的思想,而且感受到了这些思想背后的关怀以及它们与关怀我们自己的存在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由于威廉斯的许多主要作品都已被翻译,这篇介绍的中文译本无疑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詹金斯从三个环环相扣的方面立体审视威廉斯的思维s:“发展和运用一种足够复杂的心理学,以理解哲学自身历史的持续相关性,并充分意识到偶然性在多大程度上被这段历史所饱和,影响了心理学,并引发了所谓哲学的问题。” (《引言》第9页)让我们换个角度,看看这三个方面是如何歌颂威廉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的。 《伯纳德·威廉姆斯简介》 作者:(美)Mark P. Jenkins 译者:吴云飞 版本:Yiwenzhieons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文章 |孙宁侯的概念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厚描述”中得到了“厚概念”的灵感,而格尔茨则从牛津大学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那里得到了“厚概念”的灵感。赖尔的灵感。民族志研究人员和日常语言分析师已经看到了多种感知交互和多层次的意义构建ind 表面单义性。威廉姆斯试图引入这种伦理观。在《伦理学与哲学的极限》中,威廉斯将厚重的伦理概念——如怯懦、谎言、残忍、感恩等——描述为“受世界引导”(world-guiding),也是“行动引导”。厚概念包括描述性维度和规范性维度,统一、恰当,体现对事实和价值观的把握。围绕厚概念的伦理讨论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存在常识倾向,威廉姆斯并不试图为本质上不允许逻辑意义的概念提供逻辑定义。然后是描述主义态度,通过描述使用情境、表达特征和实际关系来理解概念。它并不坚持普遍且必要的逻辑结构,也不寻求某种意义的定义或还原性解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此,他从道德现实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力图在具体而复杂的人性深处进行推理,而不是急于得出过于抽象的道德理论。关于厚概念,威廉姆斯遇到了几个问题:描述和分析与厚概念有何关系?如何区分厚概念和薄概念?是否应该检查这种区别(也许没有真正的薄概念,只是不够厚的概念)?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做出诊断后,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处方。威廉姆斯指出,一个只使用厚重概念的社会——他称之为“超传统社会”——反映的是最低限度,只有当人们从所受的社会实践中回归并反思前进的道路是否正确时,才会发展出“好”或“坏”等概念。尽管威廉姆斯告诉我们“反思可以特洛伊知识”,他并不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反思的态度。相反,反思的出现不仅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是政治共同体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因此,威廉斯并不坚持任何一种道德行为的优先性,而只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从过度关注正确和善良转向厚重概念所揭示的重要维度——荣誉与耻辱的区别、背叛与忠诚的较量、无论如何,厚重的概念都是局部的;在威廉姆斯看来,道德的讨论不能集中于提出和应用理性原则,而必须转向在不断变化的生活情境中做出审慎判断和明智选择的能力,以及理解他人和他人感受的能力。回应他人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指导就变得太薄弱,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具体事物的强烈诉求和对普遍性的强烈怀疑。尽管威廉斯很欣赏亚里士多德的真理感——“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本质上是一种动物,其性格是有确定原因的,而对康德来说,人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只是一种动物”(《引言》第249页,下同),但他仍然问亚西亚“能否认识亚里士多德本质上的美德,以及“他能否合理地将这种必然性建立在某种人性观念之上”?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 1970年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983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会员,1999年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因其对哲学的重大贡献而被授予爵士爵位。、心灵哲学和政治哲学。威廉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以及他对道德本质和道德律令的探索,一度主导了西方伦理理论的思考。他的主要著作有《伦理与哲学的限度》、《可耻与必然》、《道德运气》、《功利主义:利与弊》、《真理与真诚》等。这里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个体心理发展的历史。这是威廉姆斯的哲学史学,也是他一生遵循的工作原则。在他看来,哲学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最终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他青睐R.G.的原因是科林伍德和以赛亚·伯林都具有历史意识形态倾向。与其他哲学家不同,威廉斯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提倡对哲学问题的探索。他认为如果我们把问题退回去从其历史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新”的解决方案可以是对现有解决方案的重新解释,而理论的“进步”则可以是骄傲和远见的彰显。出于羞耻和必要,威廉姆斯挑战了当代讨论中常见的进步叙事,将古希腊伦理(尤其是荷马和悲剧)视为尚未达到现代道德的原始阶段。他认为,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误解了古代伦理,忽视了其复杂性和当代意义。威廉斯在《笛卡尔》的序言中区分了思想史和哲学史:前者探索过去著作的历史背景、影响及其与当时流行思想的关系,而后者则在哲学史中进行哲学研究。思想史不会问“这意味着什么?”但是“这是什么意思?”虽然哲学的kasaythat“更喜欢ra重要且无意的当代重建”,即使它使“本质上不清楚且不完整”的事情因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理解而无法完全确定。在另一篇题为《笛卡尔与哲学史学》的文章中,威廉斯更加清晰地阐释了哲学史的重要性以及他对哲学史的看法。他认为哲学史的巨大价值在于不同历史语境的相互比较,做出某些当代的假设,认为它被假设表现出“陌生或好奇”。他写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手头现有的哲学材料,结合对历史的理解,从以前的哲学中寻找或创造一个足够陌生的哲学结构,以帮助我们质疑现状和对传统的现有理解,包括它们的材料精灵。范例。历史上不同于现在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解决方案,摧毁了时代的坚实或狭隘的思维,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理解和应对当前困境的想象空间。这让我们想起古代著名哲学家迈克尔·弗雷德提出的哲学史研究的三种路径:哲学论着(哲学Doxography)、哲学的哲学史和哲学史的历史。他将威廉姆斯(和罗素)归入第一类,认为他们延续了《论文》中第欧根尼·拉尔修斯的方法,将非过去的哲学观点视为“现代的,甚至在今天也许是站得住脚的”。至于弗雷德本人,他显然更倾向于哲学史的历史,着眼于“重建观点和立场的实际历史演变”。除此之外,我们想到了理查德。罗蒂的差异:历史重构、理性重建、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和论文集。诚然,这些哲学史研究范式可以共存,但威廉姆斯的选择是他仔细考虑以下问题的结果。最终结果:第一,如果思想的呈现总是以某种方式调用已经产生的思想,如何区分历史叙述和非历史分析?其次,当我们试图对研究对象给出清晰且连续的解释时,如何区分诚实的历史和不诚实的历史? ,它讲故事吗?最后,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在威廉斯看来,哲学史研究的焦点始终是当前的问题,而对其所采取的过程进行分析,是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理解解决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可能采取的措施:对此,哲学家们会在这段历史中给出什么理由,他们会提出什么理由?他们的思想中是否有有用的见解,他们的论点是否得到了更适当的改进?哲学史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研究哲学史不仅可以提供后见之明,还可以提供洞察力。伯纳德·威廉姆斯。道德运气是威廉姆斯用“morallyluck”来挑战康德主义、功利主义等传统伦理理论的。在他看来,道德判断不仅仅取决于行为者的欲望、努力和有意识的选择,运气——行为者无法控制的因素——往往会显着塑造外在和内在的道德评价。道德运气不仅揭示了道德生活的崩溃,展现了超越抽象原则的个人感受和生活经历,而且也让行为者的诚信和身份受到不可控因素的动摇。在《道德运气》中,威廉姆斯用画家高更的例子来展示道德防御的构成效应:高更抛弃了他的家庭y 在塔希提岛追求艺术。驱使他这么做的艺术冲动是由基因、个性、成长环境和机会塑造的。他的艺术天赋是他身上的一个本质特征。没有它,他的选择就显得粗心了。同时,高更的成功也依赖于一系列外在的或偶然的运气:他的画作可能被毁掉或被忽视,他独特的风格可能无法引起未来观众的共鸣,等等。无论如何,高更的道德立场是事后判断的。如果他失败了,他就会被谴责为自私的逃兵。幸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种道德叙事中不同种类的“运气”的作用。威廉姆斯认为,道德运气本身虽然不是道德防御,但它也是道德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关于道德的讨论不应仅仅宗教于自愿和自主的选择。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些道德选择本身,甚至实践美德的能力,都与十是运气的产物,也是命运之手给予的不均匀的礼物。真正的“实践智慧”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威廉姆斯认为,荷马的史诗和悲剧作品为道德生活提供了丰富而令人信服的理解。他发现古希腊人非常清楚运气的作用,并且他们对“道德无能力”有着深刻的理解——演员不会因为过度的承诺、实际的现实或深刻的性格特征而选择其他情况。这并不是拒绝自由决定论,而是承认塑造道德生活的实际需要,这是一种缺乏过度理性的现代道德理论的本质现实主义。威廉姆斯鼓励我们反思自欺欺人和平淡的解释性修辞,即“理性的理性主义理论”,即一个人只有能够诉诸普遍接受的规范才是理性的。他还赞赏亲自由主义者(包括他自己)认真对待理想的事实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认为程序正义和人类平等是局部的、暂时的和受文化限制的,托马斯·内格尔探讨了运气如何挑战道德运气的公平观念。这种思维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一般预设或普遍原则的不信任,以及对宏大伦理理论的怀疑。这种怀疑论与认识论怀疑论不同,因此它不是原则性怀疑论或方法论怀疑论,而是实践怀疑论。它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由可疑的证据、相互矛盾的证词或未兑现的承诺等真实因素引发,并针对某种主张或信念的可信度。同时,这样的思考也会引发对“道德”本身的反思。威廉姆斯在晚年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表示,他预计“道德运气”会成为一种“矛盾修辞法”,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说法会在道德讨论中引入一些东西。然而,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区分道德和不道德,或者更确切地说,充分探讨这种差异以及“道德”应该包含什么,是最紧迫的伦理问题。在他最后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除了聪明之外,还需要什么”时,威廉姆斯回答道,“对论点或纸面之外的事情有深刻的理解,还有一些想象力。许多哲学家以一种非常线性的方式进行,用一个证明推翻另一个证明,或者用反驳来拒绝其他假定的证明,而不是事后思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往往会忘记主要问题。一个例子是,“什么是道德考虑而不是非道德考虑?” “这些问题很深刻,并且首先不会问为什么这种差异被认为如此重要。坚定的悲观主义者詹金斯将威廉姆斯描述为“反理论家”。反理论主义者对复杂的人性、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不可控的偶然性有着深刻的洞察。 pThis 视图消除了通用视图、objec的思想和绝对的世界观,甚至消解了一切理论的合法性。他提醒我们,总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穿过秩序的缝隙,逃离试图遏制它们的理性结构。谈到伦理理论,一方面,反理论主义者和非认知主义者一样,认为伦理命题或道德陈述不是对客观真理的认知判断,因此不能判断真假。另一方面,他们更加彻底地放弃对什么是道德给出统一的答案,并认为伦理理论既是不必要的(不是理解的),也是不可取的(不合意的)。詹金斯指出,威廉斯认为“道德哲学没有理由提出任何自己有趣的理论”,他问我们“对基本道德信仰正确性的一般检验”。道德是什么,即使目前一些理论家很活跃,道德理论也不能成为一种可以与一定程度的经验现实相协调的哲学结构。结合起来,它导致了道德推理的决策方法。”。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道德运气》的结尾,他写道,怀疑主义“导致我们维持一种道德概念,但这个概念肯定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如何理解这种道德概念?詹金斯在本书的结尾提到了威廉姆斯对尼采谱系的偏爱,一种谱系。经常结合历史,以一种分析哲学会感到羞耻的方式来解释现象学、“现实主义”心理学和概念解释”,它不仅不违反“自然主义道德心理学”,而且“是解释伦理学的一种方式——也许是唯一的方式”。g 悲观主义(《伦理学与哲学的极限》作者:(英文)伯纳德·威廉姆斯 译者:陈家英 版: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 强烈的悲观主义以“信心”为关键词。失败了,信仰也能成功。相对主义并仍在努力捍卫物理现实观),他同意威廉斯的主要信念:理论的解体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理想道德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想象。鉴于威廉姆斯坚决拒绝解释和理性主义以及他的无神论倾向,这种信心的含义变得更加模糊。詹金斯指出,“也许威廉姆斯只是试图解决确定性与道德确定性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而信心这个概念是这种尝试的牺牲品。” (第 306 页)但在威廉姆斯看来,这种模糊性可能是灾难性的。面对人性的复杂性,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智慧的人必然会陷入麻木不仁的境地。然而,这并不是卡拉格深入探索的障碍,而是一种动力。玛莎·努斯鲍姆写道:“威廉姆斯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当我们放弃理论时,我们就会留下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缺乏哲学理论,但积极批判和自我批评,不被任何其他理论所左右,并且清楚地意识到作为判断基础的经验中可能存在的扭曲和等级制度。”对于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进行这种探索的意愿和能力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探索者可以犹豫,但不能天真;它们可能是不确定的,但并不肤浅。撰/孙宁编/李永波校/薛景宁
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科林·麦金称伯纳德·威廉姆斯为“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灵魂的分析哲学家”。尽管对于什么是人文主义者众说纷纭,但对威廉姆斯来说,一个称职的人文主义者必须深刻理解思想所处的历史情境,理解不同价值主张的重叠和冲突,看到人性的复杂性和正义的限度,接受和包容理论中不断溢出的异质成分。在“理论”基础上相互竞争的哲学家们认为,异质性因素是哲学必须克服的障碍。在威廉斯看来,哲学的“智慧”恰恰在于发现和尊重那些超越理论界限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丰富维度——比如忠诚、爱、遗憾、独特的个体叙事、无与伦比的失落、无与伦比的感受。的生活。在《伯纳德·威廉姆斯导论》(以下简称《导论》)这本对伯纳德·威廉姆斯思想的精彩介绍中,作者詹金斯不仅能耐心地研究剥茧的过程,还能将细节仔细地编织成一幅总体的思想图景。他不仅忠实地呈现了威廉斯思想的原貌,而且从高处做出了公正的定位,表明他既能看到树木,又能看到森林的理论实践。更重要的是,詹金斯的叙述充满温暖。在保留这本书的同时,我们不仅了解了威廉姆斯的思想,而且感受到了这些思想背后的关怀以及它们与关怀我们自己的存在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由于威廉斯的许多主要作品都已被翻译,这篇介绍的中文译本无疑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詹金斯从三个环环相扣的方面立体审视威廉斯的思维s:“发展和运用一种足够复杂的心理学,以理解哲学自身历史的持续相关性,并充分意识到偶然性在多大程度上被这段历史所饱和,影响了心理学,并引发了所谓哲学的问题。” (《引言》第9页)让我们换个角度,看看这三个方面是如何歌颂威廉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的。 《伯纳德·威廉姆斯简介》 作者:(美)Mark P. Jenkins 译者:吴云飞 版本:Yiwenzhieons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文章 |孙宁侯的概念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厚描述”中得到了“厚概念”的灵感,而格尔茨则从牛津大学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那里得到了“厚概念”的灵感。赖尔的灵感。民族志研究人员和日常语言分析师已经看到了多种感知交互和多层次的意义构建ind 表面单义性。威廉姆斯试图引入这种伦理观。在《伦理学与哲学的极限》中,威廉斯将厚重的伦理概念——如怯懦、谎言、残忍、感恩等——描述为“受世界引导”(world-guiding),也是“行动引导”。厚概念包括描述性维度和规范性维度,统一、恰当,体现对事实和价值观的把握。围绕厚概念的伦理讨论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存在常识倾向,威廉姆斯并不试图为本质上不允许逻辑意义的概念提供逻辑定义。然后是描述主义态度,通过描述使用情境、表达特征和实际关系来理解概念。它并不坚持普遍且必要的逻辑结构,也不寻求某种意义的定义或还原性解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此,他从道德现实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力图在具体而复杂的人性深处进行推理,而不是急于得出过于抽象的道德理论。关于厚概念,威廉姆斯遇到了几个问题:描述和分析与厚概念有何关系?如何区分厚概念和薄概念?是否应该检查这种区别(也许没有真正的薄概念,只是不够厚的概念)?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做出诊断后,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处方。威廉姆斯指出,一个只使用厚重概念的社会——他称之为“超传统社会”——反映的是最低限度,只有当人们从所受的社会实践中回归并反思前进的道路是否正确时,才会发展出“好”或“坏”等概念。尽管威廉姆斯告诉我们“反思可以特洛伊知识”,他并不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反思的态度。相反,反思的出现不仅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是政治共同体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因此,威廉斯并不坚持任何一种道德行为的优先性,而只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从过度关注正确和善良转向厚重概念所揭示的重要维度——荣誉与耻辱的区别、背叛与忠诚的较量、无论如何,厚重的概念都是局部的;在威廉姆斯看来,道德的讨论不能集中于提出和应用理性原则,而必须转向在不断变化的生活情境中做出审慎判断和明智选择的能力,以及理解他人和他人感受的能力。回应他人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指导就变得太薄弱,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具体事物的强烈诉求和对普遍性的强烈怀疑。尽管威廉斯很欣赏亚里士多德的真理感——“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本质上是一种动物,其性格是有确定原因的,而对康德来说,人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只是一种动物”(《引言》第249页,下同),但他仍然问亚西亚“能否认识亚里士多德本质上的美德,以及“他能否合理地将这种必然性建立在某种人性观念之上”?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 1970年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983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会员,1999年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因其对哲学的重大贡献而被授予爵士爵位。、心灵哲学和政治哲学。威廉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以及他对道德本质和道德律令的探索,一度主导了西方伦理理论的思考。他的主要著作有《伦理与哲学的限度》、《可耻与必然》、《道德运气》、《功利主义:利与弊》、《真理与真诚》等。这里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个体心理发展的历史。这是威廉姆斯的哲学史学,也是他一生遵循的工作原则。在他看来,哲学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最终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他青睐R.G.的原因是科林伍德和以赛亚·伯林都具有历史意识形态倾向。与其他哲学家不同,威廉斯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提倡对哲学问题的探索。他认为如果我们把问题退回去从其历史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新”的解决方案可以是对现有解决方案的重新解释,而理论的“进步”则可以是骄傲和远见的彰显。出于羞耻和必要,威廉姆斯挑战了当代讨论中常见的进步叙事,将古希腊伦理(尤其是荷马和悲剧)视为尚未达到现代道德的原始阶段。他认为,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误解了古代伦理,忽视了其复杂性和当代意义。威廉斯在《笛卡尔》的序言中区分了思想史和哲学史:前者探索过去著作的历史背景、影响及其与当时流行思想的关系,而后者则在哲学史中进行哲学研究。思想史不会问“这意味着什么?”但是“这是什么意思?”虽然哲学的kasaythat“更喜欢ra重要且无意的当代重建”,即使它使“本质上不清楚且不完整”的事情因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理解而无法完全确定。在另一篇题为《笛卡尔与哲学史学》的文章中,威廉斯更加清晰地阐释了哲学史的重要性以及他对哲学史的看法。他认为哲学史的巨大价值在于不同历史语境的相互比较,做出某些当代的假设,认为它被假设表现出“陌生或好奇”。他写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手头现有的哲学材料,结合对历史的理解,从以前的哲学中寻找或创造一个足够陌生的哲学结构,以帮助我们质疑现状和对传统的现有理解,包括它们的材料精灵。范例。历史上不同于现在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解决方案,摧毁了时代的坚实或狭隘的思维,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理解和应对当前困境的想象空间。这让我们想起古代著名哲学家迈克尔·弗雷德提出的哲学史研究的三种路径:哲学论着(哲学Doxography)、哲学的哲学史和哲学史的历史。他将威廉姆斯(和罗素)归入第一类,认为他们延续了《论文》中第欧根尼·拉尔修斯的方法,将非过去的哲学观点视为“现代的,甚至在今天也许是站得住脚的”。至于弗雷德本人,他显然更倾向于哲学史的历史,着眼于“重建观点和立场的实际历史演变”。除此之外,我们想到了理查德。罗蒂的差异:历史重构、理性重建、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和论文集。诚然,这些哲学史研究范式可以共存,但威廉姆斯的选择是他仔细考虑以下问题的结果。最终结果:第一,如果思想的呈现总是以某种方式调用已经产生的思想,如何区分历史叙述和非历史分析?其次,当我们试图对研究对象给出清晰且连续的解释时,如何区分诚实的历史和不诚实的历史? ,它讲故事吗?最后,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在威廉斯看来,哲学史研究的焦点始终是当前的问题,而对其所采取的过程进行分析,是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理解解决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可能采取的措施:对此,哲学家们会在这段历史中给出什么理由,他们会提出什么理由?他们的思想中是否有有用的见解,他们的论点是否得到了更适当的改进?哲学史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研究哲学史不仅可以提供后见之明,还可以提供洞察力。伯纳德·威廉姆斯。道德运气是威廉姆斯用“morallyluck”来挑战康德主义、功利主义等传统伦理理论的。在他看来,道德判断不仅仅取决于行为者的欲望、努力和有意识的选择,运气——行为者无法控制的因素——往往会显着塑造外在和内在的道德评价。道德运气不仅揭示了道德生活的崩溃,展现了超越抽象原则的个人感受和生活经历,而且也让行为者的诚信和身份受到不可控因素的动摇。在《道德运气》中,威廉姆斯用画家高更的例子来展示道德防御的构成效应:高更抛弃了他的家庭y 在塔希提岛追求艺术。驱使他这么做的艺术冲动是由基因、个性、成长环境和机会塑造的。他的艺术天赋是他身上的一个本质特征。没有它,他的选择就显得粗心了。同时,高更的成功也依赖于一系列外在的或偶然的运气:他的画作可能被毁掉或被忽视,他独特的风格可能无法引起未来观众的共鸣,等等。无论如何,高更的道德立场是事后判断的。如果他失败了,他就会被谴责为自私的逃兵。幸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种道德叙事中不同种类的“运气”的作用。威廉姆斯认为,道德运气本身虽然不是道德防御,但它也是道德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关于道德的讨论不应仅仅宗教于自愿和自主的选择。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些道德选择本身,甚至实践美德的能力,都与十是运气的产物,也是命运之手给予的不均匀的礼物。真正的“实践智慧”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威廉姆斯认为,荷马的史诗和悲剧作品为道德生活提供了丰富而令人信服的理解。他发现古希腊人非常清楚运气的作用,并且他们对“道德无能力”有着深刻的理解——演员不会因为过度的承诺、实际的现实或深刻的性格特征而选择其他情况。这并不是拒绝自由决定论,而是承认塑造道德生活的实际需要,这是一种缺乏过度理性的现代道德理论的本质现实主义。威廉姆斯鼓励我们反思自欺欺人和平淡的解释性修辞,即“理性的理性主义理论”,即一个人只有能够诉诸普遍接受的规范才是理性的。他还赞赏亲自由主义者(包括他自己)认真对待理想的事实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认为程序正义和人类平等是局部的、暂时的和受文化限制的,托马斯·内格尔探讨了运气如何挑战道德运气的公平观念。这种思维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一般预设或普遍原则的不信任,以及对宏大伦理理论的怀疑。这种怀疑论与认识论怀疑论不同,因此它不是原则性怀疑论或方法论怀疑论,而是实践怀疑论。它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由可疑的证据、相互矛盾的证词或未兑现的承诺等真实因素引发,并针对某种主张或信念的可信度。同时,这样的思考也会引发对“道德”本身的反思。威廉姆斯在晚年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表示,他预计“道德运气”会成为一种“矛盾修辞法”,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说法会在道德讨论中引入一些东西。然而,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区分道德和不道德,或者更确切地说,充分探讨这种差异以及“道德”应该包含什么,是最紧迫的伦理问题。在他最后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除了聪明之外,还需要什么”时,威廉姆斯回答道,“对论点或纸面之外的事情有深刻的理解,还有一些想象力。许多哲学家以一种非常线性的方式进行,用一个证明推翻另一个证明,或者用反驳来拒绝其他假定的证明,而不是事后思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往往会忘记主要问题。一个例子是,“什么是道德考虑而不是非道德考虑?” “这些问题很深刻,并且首先不会问为什么这种差异被认为如此重要。坚定的悲观主义者詹金斯将威廉姆斯描述为“反理论家”。反理论主义者对复杂的人性、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不可控的偶然性有着深刻的洞察。 pThis 视图消除了通用视图、objec的思想和绝对的世界观,甚至消解了一切理论的合法性。他提醒我们,总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穿过秩序的缝隙,逃离试图遏制它们的理性结构。谈到伦理理论,一方面,反理论主义者和非认知主义者一样,认为伦理命题或道德陈述不是对客观真理的认知判断,因此不能判断真假。另一方面,他们更加彻底地放弃对什么是道德给出统一的答案,并认为伦理理论既是不必要的(不是理解的),也是不可取的(不合意的)。詹金斯指出,威廉斯认为“道德哲学没有理由提出任何自己有趣的理论”,他问我们“对基本道德信仰正确性的一般检验”。道德是什么,即使目前一些理论家很活跃,道德理论也不能成为一种可以与一定程度的经验现实相协调的哲学结构。结合起来,它导致了道德推理的决策方法。”。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道德运气》的结尾,他写道,怀疑主义“导致我们维持一种道德概念,但这个概念肯定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如何理解这种道德概念?詹金斯在本书的结尾提到了威廉姆斯对尼采谱系的偏爱,一种谱系。经常结合历史,以一种分析哲学会感到羞耻的方式来解释现象学、“现实主义”心理学和概念解释”,它不仅不违反“自然主义道德心理学”,而且“是解释伦理学的一种方式——也许是唯一的方式”。g 悲观主义(《伦理学与哲学的极限》作者:(英文)伯纳德·威廉姆斯 译者:陈家英 版: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 强烈的悲观主义以“信心”为关键词。失败了,信仰也能成功。相对主义并仍在努力捍卫物理现实观),他同意威廉斯的主要信念:理论的解体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理想道德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想象。鉴于威廉姆斯坚决拒绝解释和理性主义以及他的无神论倾向,这种信心的含义变得更加模糊。詹金斯指出,“也许威廉姆斯只是试图解决确定性与道德确定性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而信心这个概念是这种尝试的牺牲品。” (第 306 页)但在威廉姆斯看来,这种模糊性可能是灾难性的。面对人性的复杂性,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智慧的人必然会陷入麻木不仁的境地。然而,这并不是卡拉格深入探索的障碍,而是一种动力。玛莎·努斯鲍姆写道:“威廉姆斯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当我们放弃理论时,我们就会留下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缺乏哲学理论,但积极批判和自我批评,不被任何其他理论所左右,并且清楚地意识到作为判断基础的经验中可能存在的扭曲和等级制度。”对于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进行这种探索的意愿和能力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探索者可以犹豫,但不能天真;它们可能是不确定的,但并不肤浅。撰/孙宁编/李永波校/薛景宁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