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020-66888888
女孩的成长,从经历各种“离别”开始|郭宇杰
作者:365bet亚洲体育 发布时间:2025-10-30 0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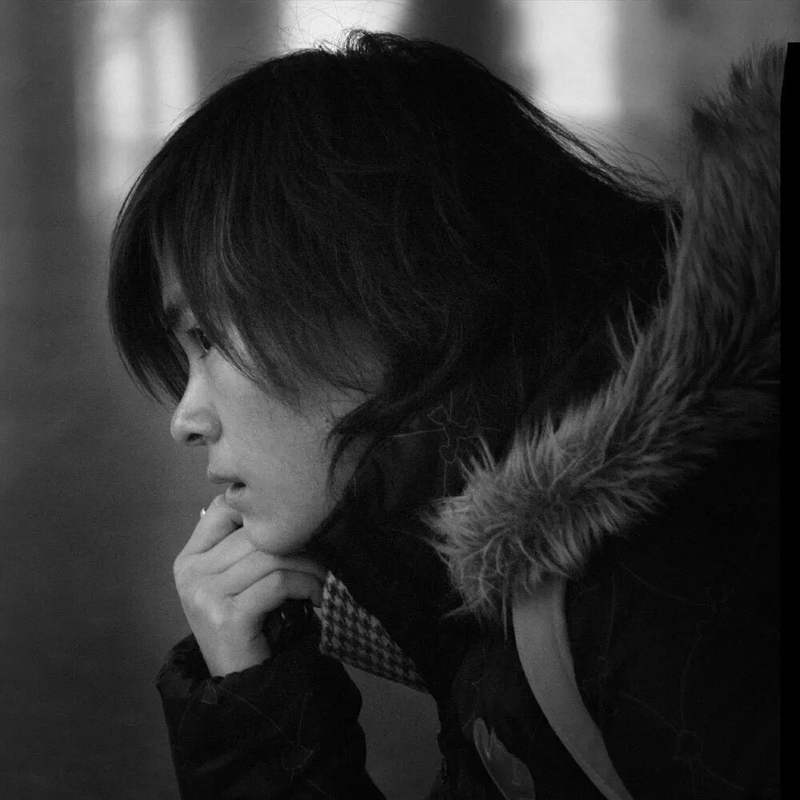 “逃跑或回头都不是答案。”当女性跑步成为人们容易谈论的话题之一时,作家郭玉洁却没有朝这个方向写作。多年来创作非小说类作品,她以记录者的视角讲述了许多普通女性的故事。在她的《我是范玉素》一书中,我们会看到一个50多年来没有被生活打垮的农村妇女;在《社会主义妇女图鉴》中,她写了一群妇女如何创办女子学校,但后来被时代遗忘的故事。但在这些叙述之外,他仍然感到“不满足”。现实生活不仅仅遵循逻辑。他想写更复杂或“更难”的主题。于是,就有了小说集《编织巴吉奥》。 《编织风暴》收录了他多年来反复书写的五个关于普通女性的故事。与大多数非小说作品中呈现的果断女性形象不同,小说中的这些女性遭遇了各种无声的压制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在很多时刻都知道不舒服,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想过要走出来。他想传播和书写所涉及的斗争,试图理解虚构世界中每一个可能的选择。先看,先不解释。他从非虚构类到虚构类的道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说服自己“我写的是小说的基础”残片。“几乎都是散落的,因为不想陷入套路,无法给人阅读的乐趣。”在她看来,在小说中写女性还是很难的,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应该做“难”的事情。新书发布之际,我们在北京遇见了郭玉洁,和她聊了聊关于女性的故事。她想写的女人生活中的“复杂”,以及他在写作中的变化和思考,这些都是他想写的东西。艺术多年。虽然他还没有有一天开始写。曾接受作家、媒体人郭玉杰的采访和撰稿。先后就职于《财经》、《单向街》更名为《单读》)、《镜头》、《正午》等媒体。出版非虚构作品集《声音》和小说集《编织风暴》。坐下后,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向了这次采访的主题。或许是因为多年的非小说创作经验,郭宇杰在谈论个人生活或创作小说时,很少以第一人称“我”开始对话。他总是在谈论其他人,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这种观点或许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的写作本身。 “从写非小说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写他人。即使在写自己的时候,我们仍然意识到‘他人’的存在。” 《编织风暴》 作者:郭玉杰 版本:新兴出版社ishing House |新经典文化2025年10月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总是在不自觉地试图“理解”。在小说集中,他关注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生活,写了年轻妻子对伴侣的失望——他经历了被风迎面而来的自由,却“无法想象没有他”;他写的是一位祖母,在孙子出生后,在大城市帮助孩子们照顾孩子——她也有羞于谈论的爱好,想要为自己而活,但她总觉得“她的背后有更大的力量”。在这些角色背后,郭宇杰表示,他仍然希望找回各自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些担忧最终指向了他想写的问题。 2017年,平和在演讲《在想象的城市里闪耀一盏灯》中谈到了他的母亲。三年饥荒期间,甘肃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我母亲的父母都饿死在家里了。我舅舅考上了师范学院,每顿饭都有一个馒头。他决定带着妹妹,和唯一的馒头住在一起。郭玉洁说,她一直对母亲这一代人感到好奇——这群女性似乎一夜之间突然获得了解放,但仍然承受着时代的灾难。然而,他仍然觉得很难写这个他想写的话题。他担心这个故事在讲述时会陷入某种陷阱,他总是犹豫着还能说些什么与当时很多人讲述的故事不同的(对读者来说)。尽管当他从非小说转向小说写作时,有些隐藏的部分是他最难克服的。采访中,他不止一次表示“感觉自己写得不好”、“好像没有天赋”。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仍然我近几年来写的。尽管抽屉里塞满了许多“毫无根据”的废稿,但他仍然觉得这种“困难”的东西对他有着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多年来,他在日常工作编辑和私人写作之间寻求平衡,让自己保持“工作”。他说有一天,他会写出他想“写”的东西。女孩的成长是从经历各种“离别”开始的。 B北京传奇:本书是五个关于普通女性的故事。在写这五个故事之前,每个故事的“灵感”或最初的想法是什么?郭玉杰:每篇文章都不一样。写《观音巷》的时候,首先出现了奶奶的形象,她的原型就是我的奶奶。和很多人一样,我小时候,祖母养育了我整整一代人。在我的记忆中,奶奶生活很艰苦,英年早逝。我一直很难理解他的死。那时我还年轻,可能刚刚进入青春期ty,我并不真正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有一天你回到家,突然有人告诉你:“奶奶去世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很久以前,我才慢慢明白电影《少女》(2025)剧照中,当你爱的人死去时的感觉。另一个角色是小鱼钩女孩。我总是想知道,女孩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许多作家都写过男孩的成长。主要情节是性意识的出现或父子关系的变化。我一直觉得女孩的成长不是这样的,而是可以从经历各种“离别”开始——长辈的去世、大家庭的去世等等。 女性亲戚要结婚的时候,身边的人从小就说“结婚了就好了”。所以我想看看,一个原本无忧无虑、无法无天的女孩是如何经历这些聚会的,又是如何成长的。文章“滑板车”从“对象”开始。有一天出门,我突然发现很多孩子好像都有一辆滑板车,在骑着,后面总是跟着一个“奶奶”。这里的奶奶不像我的奶奶。他真正受过教育,工作过,是这个国家的“建设者”。但到了晚年,一旦家里生了孩子,他们似乎就默认了对家庭的依赖。我想写另一个这样的“祖母”形象。新京报:您在《观音巷》一文中,以一个小女孩——鱼钩的视角,写了沙镇巷子里的日常生活。写下孩子无意中听到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以及他在家里看到的互动。孩子以后所能付出的一切,可能在他们刚接触的时候就已经触动过。当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是否一次又一次沿着鱼钩回到自己的童年?郭玉杰:这篇文章写完后,很多朋友看了都说他们想到了“城南旧事”。同样是小女孩的视角,不过《老江南故事》中的小女孩多少有点旁观者的视角,可能更容易看出里面的剧情。 “观音巷”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成长”。改编自《南方往事》的同名电影(1983)剧照。在这本书里,其他章节的主角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一章却有一些我自己的影子。但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仍然不是我。因为我现在,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但是鱼钩在那个年纪,我想让自己进入他的视角,一个小女孩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在那个年纪如果一个鸡巴可以对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她不明白为什么家里会发生不同的事情,大人每天谈论的事情,他们不明白。这是我的探索,如何在成年后回到童年,抛开所有的“理解”成为一个成年人,重新从一个小女孩的角度看待周围的世界。新京报:你书中的很多女性都没有名字。他们被称为“母亲”或“奶奶”,就好像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他们的名字一样。但这篇文章中的小女孩有一个名字,而且是一个听起来不太像“鱼钩”这样的名字。郭玉洁:(笑)这个名字我想了很多。鱼钩住的小镇本来就在沙漠地区,是一个非常干燥的地方,但几年前,那里还有湖泊和鱼,所以这样的名字就有一种神奇又调皮的含义,就像这个女孩的感觉。我没有说出《丛林飞翔》中这两个人的名字,因为人物之间的关系相当简单,我想这在今天的年轻情侣中很常见。没有“踏板车”的名字,是因为我注意到很多家庭有了孩子后,每个人似乎都失去了名字,变成了围绕着孩子的“职业头衔”。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种瘦弱的g。新京报:这本书确实写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处境。这些年来,当你步入中年,也看着母亲一步步走向晚年时,你对“年龄”是否也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呢?郭玉洁:当我决定写女性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这几年国内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的年龄不仅意味着自然时间、青年或老年,而且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世界观。我祖母那一代经历过饥荒和战争。那时没有节育措施,他们通常生很多孩子。到了我母亲那一代,他们努力争取教育和就业机会,但仍然受到很多观念的束缚。我这一代人有更多的自由和物质基础;而下一代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变化使世界上的每一代人都截然不同,并且周围的人不一样。有时候,当我读到一些作品时,即使是成年人,似乎他们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与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我希望我还能写出不同时代、不同时代的观点。 “好学生最怕写错答案”。新京报:《我去了2000年》就像是《观音巷》的“延续”。写一篇关于一位工作年龄女性重返大学的回忆。此时他生命中的时刻不断与当年的片段互动。他为什么要讲过去的事?郭玉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突然说:“我离婚了。”当时,所有人都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但他很自然,也很坚定:“很好,真的。”这时,另一个女孩突然说道:“我也离婚了。”其他女孩似乎慢慢的感觉到了,开始举杯向两人表示祝贺。桌上的其他男人似乎有些失落,不得不举起酒杯。多么令人惊奇的景象啊。当时我就意识到,在我们这个年纪,很多女性在婚姻中或者对婚姻的感受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记得他们步入婚姻的时候,还是做出了“不错的选择”,当时很幸福。那么近年来发生了什么?我还发现,这个时候,他们最怀念的就是校园,怀念学习的时光。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回去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呢?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电影《Kwento ng Kasal》(2019) 的剧照。北京消息:当这位中年妇女穿越时空,她遇到了很多成长轨迹与她截然不同的人。那时的“天灵”和“阿原”说起自己的野心,都是狂野而脆弱的,有着很多的欲望。他们想问:“二十年后,他们成功了吗?这一切的饥饿、退缩和等待值得吗?”这可能是每个人心里都曾一度闪过的一个念头。在你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是已经有了答案,还是你还想要答案? 郭玉洁:我对自己没有迷茫,也没有经历过饥饿和流血的感动。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很幸运,我们当时正处于所谓的“经济上升期”,相对自由,我们从这一波浪潮中受益匪浅,但即便如此,我们这一代媒体人还是很幸运的。那时候,像元这样的“艺术家”并没有处于一个向上的轨道,而是过着非常边缘的生活,其实这在当时的北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现象,但是在这个时候写下来并听到很多朋友的反馈后,我意识到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本文的主人公多莉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他努力确保自己没有迈出任何“错误”的一步。户籍、工作、买房、孩子上学……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人们常常情不自禁地为自己过去的选择辩护,“看来我只能为自己而奋斗,还能做什么呢?”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混乱的冲动,有些可能要到很多年后才会出现。这对于“好学生”来说可能是个问题。好学生最怕写错答案。新京报记者:在文章的最后,多莉说她看到了“自由和自由的代价”,并表示她“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无论是二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后,她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谈谈这种感觉吗?郭玉杰:这和我对“旅行文学”的思考有关。我总是想知道,如果人们可以回到过去,他们真的会改变什么吗,或者他们真的想改变什么吗?如果你中年之后想重返校园,你想不想做点什么?她的选择?如果他真的在小说中做出了另外的选择,那么整个世界都会改变,而不再是今天的世界,他会吗?也许回去面对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生活才更有可能。新京报:其实,你在这些文章中写到的女性,可能在某些生活中感受到了伤害,有过逃避的想法,但几乎没有人真正付诸行动。郭玉杰:这可能是人性的常态。事实上,“做出选择”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想法。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本能地行动,或者只能根据当时的条件采取某些行动,并不一定很“理性”。更何况,人不仅仅是自己,总有很多其他的关系在“干扰”,所以某种混乱和矛盾的状态就像生活一样。至于逃跑,其实从5月4日运动开始,逃跑就成了panukala。我想现阶段我更想问的是“跑到哪里去”和“跑掉后做什么””。也许奔跑或者回归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生活。从非小说到小说:最困难的是找不到《声音》的“成型”逻辑 作者:郭玉杰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月新京报:谈下写作。您在过去的非小说写作和编辑中也写过很多女性。我想,郭玉洁:关于主题,一开始确实不太确定,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当我思考一些与时代有关的事情时,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男人的形象,我明白这是我们的文学传统给我的惯性,这意味着即使我是一个女人,写女人也更加困难,所以我决定写很多困难的事情。一个一开始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无法成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说服自己“我在写小说”…… 新京报:有点意外。我印象中您多年来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非小说类报道,也做过很多编辑。您编辑出版过《我是范玉素》这样的作品,文字功底已经很强了。但短短几分钟内,你却多次提到“不成立”。在您看来,脚所谓的“垃圾稿件”与您心目中的“标准”有何不同?郭玉杰:是的,这些年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它可以追溯到非小说类和小说类两种不同的类型。其实我在非小说中写过很多关于普通人的故事,但与小说相比,非小说中的普通人“更不平凡”,因为你必须选择一个主题,说服编辑,说服读者。这个人必须有特点还有一个故事,对吧?于是就有了人物和故事。也就是说,永远是一个有特点的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事件逻辑。写作就是还原这个轮廓,填补很多细节。至于小说中的普通人,一开始并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生活是分散的、散乱的、矛盾的。你必须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你不能遵循现有的情节大纲,因为生成的事件可能意味着一个任务,而我不想进入那个例程。因此,很难在零散、碎片、矛盾的日常生活中找到整体,并塑造出不落入陷阱的形状。我认为“毫无根据”的废稿,大多都是散落的,因为它们不想陷入套路,也不能让人高兴。新京报:为什么你会关心一部小说是否“发达”或者“完整性”?郭玉杰:“诚信”的背后,我认为是对人生的理解。世界卫生大会t 是表面生命还是深层生命?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源于过去的许多时刻。 mythis 连接是什么?如果没有这种完整性,我们就只有碎片和不断更新的潮流,我们就无法真正思考很多事情。而小说仍然可以提供这样的完整性。完整、建立叙事逻辑、引人注目,使读者做好阅读准备,从阅读中获得乐趣,有一个相对完整的阅读体验。这也是我写作的追求。也许这和我的媒体经历有关。我关心读者。无论内容多么专业,我总是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并愿意阅读。如果能从中产生一些共鸣和对话就更好了。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迎合读者。尊重读者和迎合读者应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想知道我母亲的性别反应:为什么他们总是看起来“不”新京报:很多年前你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开始写我想写的东西,就像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如何度过饥荒的故事一样。”是“最想写的”开始写的吗? 郭玉洁:(笑)还没有。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仍然很难。那一代女性所面临的艰辛是今天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我仍然无法放下笔,直到我能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另一个困难是,前一代作家,比如莫言和余华,如果我想写得好,那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故事改编自《活着》的电影《Parehong Pangal》:也许“如果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对你和你的家人来说并不重要。当你母亲那一代的女性离开家庭时,你有什么感觉比以前更强烈的紧迫感?郭玉洁:也许……这些年,我母亲的兄弟姐妹去世了,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事情都变得难以记起……但我似乎还是觉得,如果我写得不好,对这件事也是一种“随意”。或许,更多的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的读者意味着什么?小时候,我不想听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讲这些故事。我发现它们非常冗长,忍不住想,“哦,再看看我们。”这种感觉至今犹在,恐怕说起来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觉。那么一切都将毫无意义。所以我要继续思考和探索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和理解方式。新京报:我记得当你在《一夕》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到要写你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时,你的思想还不是很发达。时间。它仍然是一个相当笼统和不明确的图像。你母亲那一代人的哪些方面一直吸引着你?令我好奇的是我母亲那一代——这群看似一夜之间获得解放,却依然承受着时代灾难的女性?确实,想一想,当时还是十几岁女孩的姨妈,勇敢地救了当时只有6岁的母亲。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们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也有很多简单的理念,比如自强不息、平等等。那是过去中国整整一代女性的面孔。同时,作为母亲,她们也不是传统的母亲形象。这种巨大的冲突往往意味着他们“不容易接近”。起初我很难理解他们,但渐渐地,我对他们产生了敬佩,也更加好奇了。她们之间的冲突是巨大的,这种内心的冲突可能仍然存在于我们这些年轻女性中。虽然每一代女性虽然处境不同,他们也有不同的境遇,但他们仍然有很多内在的遗传性和共同的命运。相似中的差异就是我想写的。撰稿/沉璐编辑/希希/刘宝庆校对
“逃跑或回头都不是答案。”当女性跑步成为人们容易谈论的话题之一时,作家郭玉洁却没有朝这个方向写作。多年来创作非小说类作品,她以记录者的视角讲述了许多普通女性的故事。在她的《我是范玉素》一书中,我们会看到一个50多年来没有被生活打垮的农村妇女;在《社会主义妇女图鉴》中,她写了一群妇女如何创办女子学校,但后来被时代遗忘的故事。但在这些叙述之外,他仍然感到“不满足”。现实生活不仅仅遵循逻辑。他想写更复杂或“更难”的主题。于是,就有了小说集《编织巴吉奥》。 《编织风暴》收录了他多年来反复书写的五个关于普通女性的故事。与大多数非小说作品中呈现的果断女性形象不同,小说中的这些女性遭遇了各种无声的压制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在很多时刻都知道不舒服,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想过要走出来。他想传播和书写所涉及的斗争,试图理解虚构世界中每一个可能的选择。先看,先不解释。他从非虚构类到虚构类的道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说服自己“我写的是小说的基础”残片。“几乎都是散落的,因为不想陷入套路,无法给人阅读的乐趣。”在她看来,在小说中写女性还是很难的,但她仍然觉得自己应该做“难”的事情。新书发布之际,我们在北京遇见了郭玉洁,和她聊了聊关于女性的故事。她想写的女人生活中的“复杂”,以及他在写作中的变化和思考,这些都是他想写的东西。艺术多年。虽然他还没有有一天开始写。曾接受作家、媒体人郭玉杰的采访和撰稿。先后就职于《财经》、《单向街》更名为《单读》)、《镜头》、《正午》等媒体。出版非虚构作品集《声音》和小说集《编织风暴》。坐下后,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向了这次采访的主题。或许是因为多年的非小说创作经验,郭宇杰在谈论个人生活或创作小说时,很少以第一人称“我”开始对话。他总是在谈论其他人,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这种观点或许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的写作本身。 “从写非小说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写他人。即使在写自己的时候,我们仍然意识到‘他人’的存在。” 《编织风暴》 作者:郭玉杰 版本:新兴出版社ishing House |新经典文化2025年10月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总是在不自觉地试图“理解”。在小说集中,他关注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生活,写了年轻妻子对伴侣的失望——他经历了被风迎面而来的自由,却“无法想象没有他”;他写的是一位祖母,在孙子出生后,在大城市帮助孩子们照顾孩子——她也有羞于谈论的爱好,想要为自己而活,但她总觉得“她的背后有更大的力量”。在这些角色背后,郭宇杰表示,他仍然希望找回各自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些担忧最终指向了他想写的问题。 2017年,平和在演讲《在想象的城市里闪耀一盏灯》中谈到了他的母亲。三年饥荒期间,甘肃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我母亲的父母都饿死在家里了。我舅舅考上了师范学院,每顿饭都有一个馒头。他决定带着妹妹,和唯一的馒头住在一起。郭玉洁说,她一直对母亲这一代人感到好奇——这群女性似乎一夜之间突然获得了解放,但仍然承受着时代的灾难。然而,他仍然觉得很难写这个他想写的话题。他担心这个故事在讲述时会陷入某种陷阱,他总是犹豫着还能说些什么与当时很多人讲述的故事不同的(对读者来说)。尽管当他从非小说转向小说写作时,有些隐藏的部分是他最难克服的。采访中,他不止一次表示“感觉自己写得不好”、“好像没有天赋”。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仍然我近几年来写的。尽管抽屉里塞满了许多“毫无根据”的废稿,但他仍然觉得这种“困难”的东西对他有着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多年来,他在日常工作编辑和私人写作之间寻求平衡,让自己保持“工作”。他说有一天,他会写出他想“写”的东西。女孩的成长是从经历各种“离别”开始的。 B北京传奇:本书是五个关于普通女性的故事。在写这五个故事之前,每个故事的“灵感”或最初的想法是什么?郭玉杰:每篇文章都不一样。写《观音巷》的时候,首先出现了奶奶的形象,她的原型就是我的奶奶。和很多人一样,我小时候,祖母养育了我整整一代人。在我的记忆中,奶奶生活很艰苦,英年早逝。我一直很难理解他的死。那时我还年轻,可能刚刚进入青春期ty,我并不真正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有一天你回到家,突然有人告诉你:“奶奶去世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很久以前,我才慢慢明白电影《少女》(2025)剧照中,当你爱的人死去时的感觉。另一个角色是小鱼钩女孩。我总是想知道,女孩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许多作家都写过男孩的成长。主要情节是性意识的出现或父子关系的变化。我一直觉得女孩的成长不是这样的,而是可以从经历各种“离别”开始——长辈的去世、大家庭的去世等等。 女性亲戚要结婚的时候,身边的人从小就说“结婚了就好了”。所以我想看看,一个原本无忧无虑、无法无天的女孩是如何经历这些聚会的,又是如何成长的。文章“滑板车”从“对象”开始。有一天出门,我突然发现很多孩子好像都有一辆滑板车,在骑着,后面总是跟着一个“奶奶”。这里的奶奶不像我的奶奶。他真正受过教育,工作过,是这个国家的“建设者”。但到了晚年,一旦家里生了孩子,他们似乎就默认了对家庭的依赖。我想写另一个这样的“祖母”形象。新京报:您在《观音巷》一文中,以一个小女孩——鱼钩的视角,写了沙镇巷子里的日常生活。写下孩子无意中听到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以及他在家里看到的互动。孩子以后所能付出的一切,可能在他们刚接触的时候就已经触动过。当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是否一次又一次沿着鱼钩回到自己的童年?郭玉杰:这篇文章写完后,很多朋友看了都说他们想到了“城南旧事”。同样是小女孩的视角,不过《老江南故事》中的小女孩多少有点旁观者的视角,可能更容易看出里面的剧情。 “观音巷”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成长”。改编自《南方往事》的同名电影(1983)剧照。在这本书里,其他章节的主角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一章却有一些我自己的影子。但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仍然不是我。因为我现在,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但是鱼钩在那个年纪,我想让自己进入他的视角,一个小女孩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在那个年纪如果一个鸡巴可以对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她不明白为什么家里会发生不同的事情,大人每天谈论的事情,他们不明白。这是我的探索,如何在成年后回到童年,抛开所有的“理解”成为一个成年人,重新从一个小女孩的角度看待周围的世界。新京报:你书中的很多女性都没有名字。他们被称为“母亲”或“奶奶”,就好像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他们的名字一样。但这篇文章中的小女孩有一个名字,而且是一个听起来不太像“鱼钩”这样的名字。郭玉洁:(笑)这个名字我想了很多。鱼钩住的小镇本来就在沙漠地区,是一个非常干燥的地方,但几年前,那里还有湖泊和鱼,所以这样的名字就有一种神奇又调皮的含义,就像这个女孩的感觉。我没有说出《丛林飞翔》中这两个人的名字,因为人物之间的关系相当简单,我想这在今天的年轻情侣中很常见。没有“踏板车”的名字,是因为我注意到很多家庭有了孩子后,每个人似乎都失去了名字,变成了围绕着孩子的“职业头衔”。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种瘦弱的g。新京报:这本书确实写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处境。这些年来,当你步入中年,也看着母亲一步步走向晚年时,你对“年龄”是否也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呢?郭玉洁:当我决定写女性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这几年国内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的年龄不仅意味着自然时间、青年或老年,而且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世界观。我祖母那一代经历过饥荒和战争。那时没有节育措施,他们通常生很多孩子。到了我母亲那一代,他们努力争取教育和就业机会,但仍然受到很多观念的束缚。我这一代人有更多的自由和物质基础;而下一代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变化使世界上的每一代人都截然不同,并且周围的人不一样。有时候,当我读到一些作品时,即使是成年人,似乎他们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与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我希望我还能写出不同时代、不同时代的观点。 “好学生最怕写错答案”。新京报:《我去了2000年》就像是《观音巷》的“延续”。写一篇关于一位工作年龄女性重返大学的回忆。此时他生命中的时刻不断与当年的片段互动。他为什么要讲过去的事?郭玉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突然说:“我离婚了。”当时,所有人都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但他很自然,也很坚定:“很好,真的。”这时,另一个女孩突然说道:“我也离婚了。”其他女孩似乎慢慢的感觉到了,开始举杯向两人表示祝贺。桌上的其他男人似乎有些失落,不得不举起酒杯。多么令人惊奇的景象啊。当时我就意识到,在我们这个年纪,很多女性在婚姻中或者对婚姻的感受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记得他们步入婚姻的时候,还是做出了“不错的选择”,当时很幸福。那么近年来发生了什么?我还发现,这个时候,他们最怀念的就是校园,怀念学习的时光。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回去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呢?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电影《Kwento ng Kasal》(2019) 的剧照。北京消息:当这位中年妇女穿越时空,她遇到了很多成长轨迹与她截然不同的人。那时的“天灵”和“阿原”说起自己的野心,都是狂野而脆弱的,有着很多的欲望。他们想问:“二十年后,他们成功了吗?这一切的饥饿、退缩和等待值得吗?”这可能是每个人心里都曾一度闪过的一个念头。在你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是已经有了答案,还是你还想要答案? 郭玉洁:我对自己没有迷茫,也没有经历过饥饿和流血的感动。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很幸运,我们当时正处于所谓的“经济上升期”,相对自由,我们从这一波浪潮中受益匪浅,但即便如此,我们这一代媒体人还是很幸运的。那时候,像元这样的“艺术家”并没有处于一个向上的轨道,而是过着非常边缘的生活,其实这在当时的北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现象,但是在这个时候写下来并听到很多朋友的反馈后,我意识到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本文的主人公多莉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他努力确保自己没有迈出任何“错误”的一步。户籍、工作、买房、孩子上学……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人们常常情不自禁地为自己过去的选择辩护,“看来我只能为自己而奋斗,还能做什么呢?”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混乱的冲动,有些可能要到很多年后才会出现。这对于“好学生”来说可能是个问题。好学生最怕写错答案。新京报记者:在文章的最后,多莉说她看到了“自由和自由的代价”,并表示她“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无论是二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后,她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谈谈这种感觉吗?郭玉杰:这和我对“旅行文学”的思考有关。我总是想知道,如果人们可以回到过去,他们真的会改变什么吗,或者他们真的想改变什么吗?如果你中年之后想重返校园,你想不想做点什么?她的选择?如果他真的在小说中做出了另外的选择,那么整个世界都会改变,而不再是今天的世界,他会吗?也许回去面对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生活才更有可能。新京报:其实,你在这些文章中写到的女性,可能在某些生活中感受到了伤害,有过逃避的想法,但几乎没有人真正付诸行动。郭玉杰:这可能是人性的常态。事实上,“做出选择”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想法。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本能地行动,或者只能根据当时的条件采取某些行动,并不一定很“理性”。更何况,人不仅仅是自己,总有很多其他的关系在“干扰”,所以某种混乱和矛盾的状态就像生活一样。至于逃跑,其实从5月4日运动开始,逃跑就成了panukala。我想现阶段我更想问的是“跑到哪里去”和“跑掉后做什么””。也许奔跑或者回归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生活。从非小说到小说:最困难的是找不到《声音》的“成型”逻辑 作者:郭玉杰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月新京报:谈下写作。您在过去的非小说写作和编辑中也写过很多女性。我想,郭玉洁:关于主题,一开始确实不太确定,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当我思考一些与时代有关的事情时,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男人的形象,我明白这是我们的文学传统给我的惯性,这意味着即使我是一个女人,写女人也更加困难,所以我决定写很多困难的事情。一个一开始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无法成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说服自己“我在写小说”…… 新京报:有点意外。我印象中您多年来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非小说类报道,也做过很多编辑。您编辑出版过《我是范玉素》这样的作品,文字功底已经很强了。但短短几分钟内,你却多次提到“不成立”。在您看来,脚所谓的“垃圾稿件”与您心目中的“标准”有何不同?郭玉杰:是的,这些年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它可以追溯到非小说类和小说类两种不同的类型。其实我在非小说中写过很多关于普通人的故事,但与小说相比,非小说中的普通人“更不平凡”,因为你必须选择一个主题,说服编辑,说服读者。这个人必须有特点还有一个故事,对吧?于是就有了人物和故事。也就是说,永远是一个有特点的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事件逻辑。写作就是还原这个轮廓,填补很多细节。至于小说中的普通人,一开始并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生活是分散的、散乱的、矛盾的。你必须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你不能遵循现有的情节大纲,因为生成的事件可能意味着一个任务,而我不想进入那个例程。因此,很难在零散、碎片、矛盾的日常生活中找到整体,并塑造出不落入陷阱的形状。我认为“毫无根据”的废稿,大多都是散落的,因为它们不想陷入套路,也不能让人高兴。新京报:为什么你会关心一部小说是否“发达”或者“完整性”?郭玉杰:“诚信”的背后,我认为是对人生的理解。世界卫生大会t 是表面生命还是深层生命?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源于过去的许多时刻。 mythis 连接是什么?如果没有这种完整性,我们就只有碎片和不断更新的潮流,我们就无法真正思考很多事情。而小说仍然可以提供这样的完整性。完整、建立叙事逻辑、引人注目,使读者做好阅读准备,从阅读中获得乐趣,有一个相对完整的阅读体验。这也是我写作的追求。也许这和我的媒体经历有关。我关心读者。无论内容多么专业,我总是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并愿意阅读。如果能从中产生一些共鸣和对话就更好了。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迎合读者。尊重读者和迎合读者应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想知道我母亲的性别反应:为什么他们总是看起来“不”新京报:很多年前你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开始写我想写的东西,就像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如何度过饥荒的故事一样。”是“最想写的”开始写的吗? 郭玉洁:(笑)还没有。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仍然很难。那一代女性所面临的艰辛是今天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我仍然无法放下笔,直到我能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另一个困难是,前一代作家,比如莫言和余华,如果我想写得好,那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故事改编自《活着》的电影《Parehong Pangal》:也许“如果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对你和你的家人来说并不重要。当你母亲那一代的女性离开家庭时,你有什么感觉比以前更强烈的紧迫感?郭玉洁:也许……这些年,我母亲的兄弟姐妹去世了,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事情都变得难以记起……但我似乎还是觉得,如果我写得不好,对这件事也是一种“随意”。或许,更多的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的读者意味着什么?小时候,我不想听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讲这些故事。我发现它们非常冗长,忍不住想,“哦,再看看我们。”这种感觉至今犹在,恐怕说起来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觉。那么一切都将毫无意义。所以我要继续思考和探索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和理解方式。新京报:我记得当你在《一夕》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到要写你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时,你的思想还不是很发达。时间。它仍然是一个相当笼统和不明确的图像。你母亲那一代人的哪些方面一直吸引着你?令我好奇的是我母亲那一代——这群看似一夜之间获得解放,却依然承受着时代灾难的女性?确实,想一想,当时还是十几岁女孩的姨妈,勇敢地救了当时只有6岁的母亲。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们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也有很多简单的理念,比如自强不息、平等等。那是过去中国整整一代女性的面孔。同时,作为母亲,她们也不是传统的母亲形象。这种巨大的冲突往往意味着他们“不容易接近”。起初我很难理解他们,但渐渐地,我对他们产生了敬佩,也更加好奇了。她们之间的冲突是巨大的,这种内心的冲突可能仍然存在于我们这些年轻女性中。虽然每一代女性虽然处境不同,他们也有不同的境遇,但他们仍然有很多内在的遗传性和共同的命运。相似中的差异就是我想写的。撰稿/沉璐编辑/希希/刘宝庆校对 下一篇:没有了

